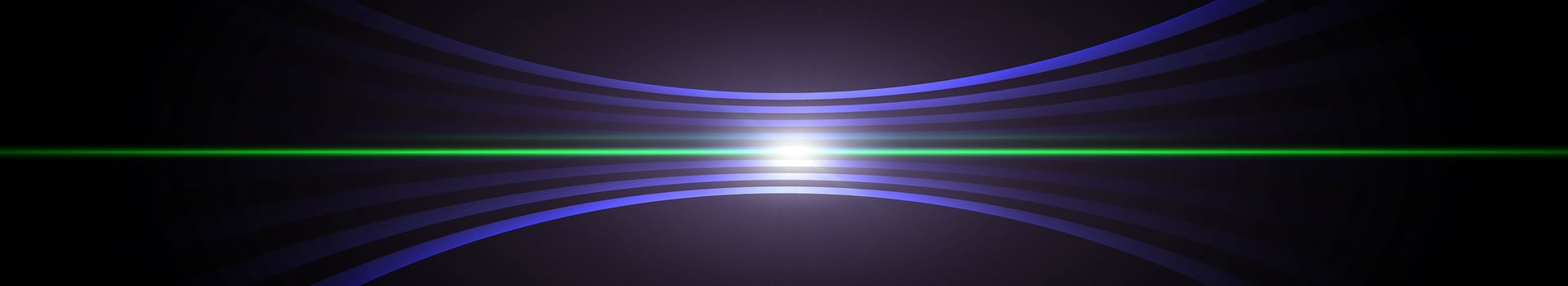
引言:一封寄往中南海的特殊家书
1949年夏末,北平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火常常彻夜通明。在筹备开国大典的万千头绪中,一封来自香港的私人信件被加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。
信封上的字迹苍劲有力,透着军人特有的风骨,但笔锋在收尾处却微微颤抖,显露出写信人内心的不平静。
署名是“卫立煌”。

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,拆开了这封信。信纸不厚,承载的情感却重逾千斤。信中,这位曾经统帅千军万马的国民党高级将领,姿态放得极低,字里行间满是恳切与无奈:
“润之我兄:
暌违多年,世事浮沉,恍如隔世。今我栖身香江,前途未卜,本无颜面向我兄提出任何请求。奈何家母年迈,独居合肥老家,日夜悬念,寝食难安。合肥今已解放,我虽不能亲奉汤药,拳拳孝心,时刻挂怀。
回想抗战烽火岁月,你我两党虽有政见之别,然于民族大义之前,曾并肩抗敌,情分尚在。尤其忻口一役,得贵军鼎力相助,立煌至今感念。
斗胆以此旧情,恳请润之我兄,能在百忙之中稍加过问,关照家母一二,使其晚年得一安稳。若能如此,立煌纵使身在天涯,亦感激不尽。
弟 卫立煌 顿首”
毛泽东读完信,沉默了许久。他指间的香烟燃尽了长长一截烟灰,却没有弹落。

他仿佛透过这封信,看到了那个在抗日战场上英姿勃发,却在解放战争中进退失据,最终流落异乡的复杂身影。
他想起了1938年延安窑洞外那个寒冷的夜晚,以及那件自己亲手为卫立煌披上的中山装。
“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。”毛泽东喃喃自语。他随即拿起笔,亲自拟定电报,发往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:“卫立煌家母尚在合肥,请予妥善安置,予以生活上之照顾,勿使其感到困难。此为统战工作,务必办好。”
这封信,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之门。卫立煌为何会在开国大典前夕,向自己昔日的“对手”写下这样一封近乎托孤的信?这一切,还要从一年前那个肃杀的深秋说起。
第一章:沈阳孤城,将军的末路悲歌
1948年10月的沈阳,秋意已深,寒意刺骨。北风像无家可归的野狗,卷着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煤灰和街头散落的枯叶,在城市的每一条巷弄里疯狂打转。
东北“剿匪”总司令部的院子里,卫兵的口令声被风吹得支离破碎。
卫立煌身着笔挺的将官呢服,双手背在身后,站在二楼司令部的巨幅玻璃窗前,神情凝重地俯瞰着楼下操场上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士兵。

这些士兵大多是刚补充进来的新兵,脸上还带着东北庄稼汉的淳朴与茫然。
他们手中的美式步枪在夕阳的余晖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,但这光芒却无法照亮他们眼神深处的疲惫与恐惧。战争的阴影,如同沈阳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,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“总座,南京特急电。”副官陈铁的声音打破了沉寂。他双手捧着一份电报,快步走到卫立煌身后,封皮上“蒋中正”三个字的亲笔签名龙飞凤舞,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压迫感。
卫立煌缓缓转过身,接过电报。他没有立刻拆开,只是用手指摩挲着封皮,他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。
这几天,这样的电报雪片般从南京飞来,内容无一例外。他撕开信封,目光迅速扫过电文,嘴角不由自主地浮起一丝冰冷的苦笑。

“呵,又是催我亲率沈阳主力,即刻出辽西,解锦州之围。”他将电报纸“啪”地一声拍在宽大的作战地图上,动作之大,震得桌角的砚台都跳了一下。
饱含墨汁的笔洗随之倾倒,乌黑的墨汁泼洒而出,在地图上迅速晕开,不偏不倚,正好将“锦州”这个让他心力交瘁的地名完全覆盖,仿佛一个不祥的预兆。
剿总参谋长赵家骧闻声凑了过来,压低声音说:“总座,这次委座是真的动怒了。电报里措辞严厉,说您‘行动迟缓,坐视友军被围,是为通敌’,甚至……甚至说您‘被林彪吓破了胆’。”
“吓破了胆?”卫立煌猛地转身,腰间的指挥刀刀鞘撞在红木桌角,发出一声沉闷而清脆的撞击声,在寂静的办公室里回响。“他懂什么!他坐在南京的安乐窝里,对着地图指手画脚,他知道辽西走廊现在是什么情况吗?”
卫立煌的怒火终于被点燃,他一把抓起桌上的指挥棒,重重地戳在地图上塔山、黑山一线。“林彪在塔山、黑山一线布下了超过十万人的阻击部队,挖了三道防线,把那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口袋!我们现在把沈阳的主力拉出去,不是去解围,是去送死!是把东北最后的本钱,亲手送到林彪的口袋里去!”

他指着地图上那条被墨迹污染的北宁线,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:“锦州,是东北的咽喉,没错!但现在咽喉已经被掐住了,范汉杰的十万大军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我们要做的是巩固沈阳,依托长春,南北呼应,把林彪拖在辽西,让他消化不良!而不是现在冲上去,被他一口吃掉!锦州失守是早晚的事,但只要沈阳主力在,东北就在!主力要是没了,东北就彻底完了!”
他的话语掷地有声,充满了战略家的清醒与无奈。然而,在千里之外的南京,这番苦心孤诣的分析,被解读为怯战和抗命。
那天深夜,南京黄埔路官邸的书房里,灯火通明。蒋介石握着电话听筒,青筋在额角突突直跳,声音里压抑着火山爆发前的怒火:“俊如(卫立煌字),你是不是要抗命到底?我命令你,立刻出兵!这是命令!”
电话另一头,卫立煌站在窗前,沈阳城的灯火在寒夜中稀稀拉拉,如同风中残烛,随时可能熄灭。他握着冰冷的话筒,手背上的青筋同样暴起:“委员长,恕难从命!这不是抗命,这是为党国保留最后一点元气!共军现在是典型的围点打援,我们不能上这个当!”
“放肆!”电话那头传来蒋介石的雷霆之怒,“我再问你一遍,你出不出兵?锦州若失,你就是千古罪人!我必将你军法从事!”

“委员长……”卫立煌还想解释,但电话那头已经传来了“嘟嘟”的忙音。
他颓然地挂了电话,沉重地靠在椅背上,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。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,像是在为这座孤城倒计时。
他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块老旧的怀表,这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时,亲手赠予他的。表盖上有一道明显的划痕,那是1937年忻口会战时,日军的弹片擦过的痕迹。
他轻轻打开表盖,看着里面仍在精准走动的指针,仿佛看到了孙先生那双充满期许的眼睛。“先生,您说,这仗到底该怎么打?”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,声音里充满了迷茫和凄凉。他一生戎马,从北伐名将到抗日英雄,何曾像今天这样,被自己人逼到如此绝境。
几天后,锦州失守的消息如同丧钟,敲响在沈阳“剿总”的每一个角落。卫立煌正在指挥所里研究最新的战报,一名参谋神色慌张、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,甚至忘了行礼:“总座,锦州……锦州在31个小时前……已经……丢了!范汉杰司令官被俘!”
卫立煌手中的钢笔“啪嗒”一声掉落在地,墨水在文件上晕开一片狼藉。他没有暴怒,也没有惊慌,只是静静地站着,仿佛一尊雕像。良久,他才缓缓吐出几个字:“沈阳,守不住了。”
他转过身,对一直侍立在旁的副官陈铁说:“准备飞机,去北平。这里,交给第九兵团的廖耀湘吧,希望他……能听我的,从营口撤退。”
然而他心中清楚,廖耀湘同样会收到来自南京的命令,命令他西进夺回锦州。东北的命运,似乎已经注定。
当卫立煌的专机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时,华北“剿总”司令傅作义早已在寒风中等候。

看到卫立煌走下舷梯,傅作义快步上前,把他拉到一边,神情复杂地低声说:“俊如兄,你这次恐怕难逃追责。蒋先生的脾气,你比我清楚。东北失守的责任,总要有人来背。”
卫立煌望着远处北平巍峨的城墙,灰色的砖石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肃穆。
他想起了十一年前,在忻口指挥台儿庄大捷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会战,那时他和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并肩抗敌,何等意气风发。谁能想到,十一年后,他会落到这般田地。
“宜生(傅作义字),”他苦笑着拍了拍傅作义的肩膀,“你我这些人,说到底,终究不过是棋盘上的棋子罢了。棋手的输赢,却要棋子来承担。”
果不其然,随着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的惨败告终,卫立煌成了头号替罪羊。
1949年初,他被蒋介石召至南京,名为述职,实为软禁。当冰冷的手铐“咔哒”一声锁住他的手腕时,他没有挣扎,只是平静地望着眼前那些神情紧张的军统特务,忽然笑了,笑声中带着无尽的苍凉:“想当年,我在缅甸的丛林里,带着弟兄们追着日本鬼子打,九死一生。没想到今天,却被自己人像犯人一样抓起来。”
第二章:金陵囚笼,风雨夜的逃亡
南京,玄武湖畔的一座西式小洋楼,成了卫立煌的囚笼。这里环境清幽,风景秀丽,但在卫立煌眼中,再美的景色也与监狱无异。

院墙外,军统特务三步一岗,五步一哨,甚至在院子的角落里架起了轻机枪,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着这栋小楼。他每天的活动范围,仅限于这方寸之间的院落。
软禁的生活,比他想象的还要难熬。身体上的禁锢尚可忍受,精神上的折磨却如附骨之疽。
报纸上,铺天盖地都是将他描绘成“通共”、“怯战”的罪魁祸首的文章。昔日的同僚故旧,避之唯恐不及。他成了一座孤岛。
只有妻子韩权华,始终陪伴在他身边,给予他无言的慰藉。韩权华出身名门,知书达理,见惯了宦海沉浮。她每天为卫立煌准备可口的饭菜,陪他在院子里散步,夜晚则为他读报解闷。
一个清冷的深夜,月光如水银泻地,洒在院中的草坪上。卫立煌站在二楼的窗前,望着天边那轮残月,久久不语。韩权华从身后为他披上一件外衣,轻声说:“夜深了,风大,当心着凉。”

卫立煌回过头,握住妻子的手,眼中流露出一丝罕见的脆弱:“权华,你说,当年在延安,毛泽东诚心留我,我要是当初就留在那里,会不会……是另一番光景?”
韩权华轻轻握紧他的手,柔声安慰道:“历史没有如果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,在当时都是你认为最正确的。别想了,时局变化这么快,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办法,或者说机会,终于在1949年4月悄然而至。
随着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,南京解放,蒋介石败退台湾,李宗仁出任代总统,力主与中共和谈。南京城内一度混乱的局势,以及李宗仁对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清洗,使得看守卫立煌的军统特务们人心惶惶,看管也日渐松懈。
一直在暗中为营救卫立煌奔走的旧部,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。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,整个南京城都笼罩在哗哗的雨声和滚滚的雷声之中。这样的天气,是逃亡的天然屏障。
深夜,接应的人化装成水电修理工,敲开了小楼的后门。卫立煌早已在韩权华的帮助下,换上了一身朴素的商人行头——一件半旧的蓝布长衫,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斗笠。
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囚禁了他数月的地方,没有丝毫留恋,拉着韩权华的手,跟着接应的人,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。

雨下得极大,豆大的雨点砸在斗笠上,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。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泞的小巷中穿行,雨水很快湿透了他们的衣衫。
街上空无一人,只有昏黄的路灯在风雨中摇曳,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。每一次远处传来的汽车声,都让他们心头一紧。
终于,他们上了一辆预先等候的黑色轿车。汽车在雨幕中疾驰,将那座囚笼远远地甩在身后。当火车缓缓驶出南京站的站台时,卫立煌才稍稍松了口气。
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窗帘的一角,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、在雨夜中模糊不清的城市灯火,心中五味杂陈。这里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,是他效忠了半生的地方,如今却要以这种方式仓皇辞别。
“再见了,南京。”他轻声说,仿佛在告别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,“也再见了,蒋先生。”
火车一路向南,最终,他们辗转抵达了当时尚属英国管治的香港。
第三章:香江浮萍,从上将到“普通人”
香港的夏天,湿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。空气中弥漫着海水、鱼腥和各种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。
对于从北方来的卫立煌夫妇而言,这种气候尤其难熬。他们租住在九龙一间狭小的公寓里,昔日门庭若市的卫公馆,变成了眼前这不足三十平米的一室一厅。

英雄末路,最先感受到的便是生活的窘迫。他们从南京逃出时,行色匆匆,并未携带多少金银。坐吃山空的日子没过多久,生活便陷入了困境。曾经指挥千军万马、手握亿万军费的上将,如今却要为一日三餐而发愁。
一天下午,卫立煌换上一件褪了色的长衫,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,尽管衣着寒酸,但那份军人的挺拔气度依然存在。他走进一家位于街角的当铺,柜台高高在上,掌柜的坐在里面,懒洋洋地打着算盘。
卫立煌从怀里掏出那块孙中山先生所赠的金壳怀表,小心翼翼地放在铺着红色绒布的柜台上,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:“老板,这块表,想当五百港币。”
掌柜的拿起怀表,取出放大镜,对着光线仔细端详了半天,点了点头:“嗯,瑞士名厂的货,金壳,机芯也不错。不过嘛,现在时局不稳,兵荒马乱的,这种东西不好出手。最多给你三百。”

“三百?”卫立煌皱起了眉头,这块表对他意义非凡,若非万不得已,他绝不会拿出来。三百港币,实在太低了。
他正想开口争辩几句,当铺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。几个穿着时髦西装、一看就非富即贵的男人闯了进来。其中一个年轻人无意中瞥了卫立煌一眼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震惊,他失声惊呼:“您……您是卫总司令?”
卫立煌心里猛地一沉,如同被一块巨石砸中。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他赶紧压低帽檐,用浓重的安徽乡音含糊地回应:“先生,你认错人了,我是做南北药材生意的。”说完,他不再计较价格,抓起柜台上的三百港币,转身就往外快步走去。背后,还传来那个年轻人和掌柜的嘀咕声:“怎么会认错,绝对是卫立煌将军……”
回到狭小的住处,韩权华正在灯下缝补一件旧衣服。看到丈夫脸色苍白,神情慌张,忙放下手中的针线,迎上来问:“怎么了?出什么事了?”

“被人认出来了。”卫立煌摘下帽子,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,不知是热的还是惊的。“以后,我们尽量少出门,尤其不要去人多的地方。香港鱼龙混杂,国民党的特务到处都是。”
这次遭遇,让他们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。他们不仅要面对贫困,还要时刻提防来自台湾的监视和可能的暗杀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韩权华希望尽快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,却轻信了一个自称有门路、可以低价代购黄金的同乡商人。
她将家里仅存的最后一点积蓄,加上当掉怀表的钱,全部投了进去。结果,那个所谓的“同乡”拿到钱后,便人间蒸发,再无踪影。
当意识到被骗时,韩权华崩溃了,她伏在桌上失声痛哭:“俊如,我对不起你……我把我们最后的钱都弄丢了……”
卫立煌看着妻子悲痛欲绝的样子,心中虽然也充满了失望和苦涩,但他没有一句责备。他走过去,轻轻拍着妻子的肩膀,长叹一口气:“算了,破财免灾吧。钱没了可以再想办法,人没事就好。”他走到窗边,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,几个行迹可疑、戴着墨镜的身影在街角一闪而过。“反正,我们现在最不缺的,就是时间。”

那段日子,是卫立煌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。为了避人耳目,他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,混迹在龙蛇混杂的平民茶楼里,一坐就是半天,只点一壶最便宜的茶。
有一次,他在茶楼里偶遇了一位曾在自己麾下任职的团长。那位旧部看到他如今的模样,又惊又悲,刚要起身敬礼,被卫立煌一个严厉的眼色制止了。
两人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,用几乎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交谈。
“总座,您……您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?”旧部眼圈泛红,声音哽咽。
卫立煌苦笑了一下,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粗劣的茶水:“这不也挺好吗?不用再为打打杀杀的事情烦心了。”他指了指窗外那些为生计奔波的普通市民,“你看那些老百姓,虽然生活清贫,但活得踏实,不用担心明天脑袋还在不在脖子上。”
就在卫立煌几乎陷入绝望之际,一缕曙光从北方传来。1954年秋的一天,他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、邮戳来自广州的信。他疑惑地拆开,只见信纸上是几行熟悉而刚劲的毛笔字:“俊如先生:别来无恙?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,欢迎你回来。 周恩来”
短短一句话,却如同一道惊雷,在卫立煌心中炸响。他握着信纸的手,抑制不住地剧烈颤抖起来。“太原结识的朋友”,这指的是1938年他与周恩来、朱德在太原彻夜长谈,共商抗日大计的往事。共产党没有忘记他!

韩权华凑过来,看到信的内容和落款,也激动得热泪盈眶:“是周先生的信!他们还记得你!”
“嗯。”卫立煌重重地点了点头,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焰,“他还记得……他还记得当年在太原的彻夜长谈。”
几乎就在同时,蒋介石也得到了卫立煌在香港的消息。很快,一名国民党特使带着重金和蒋介石的亲笔信找上门来。
特使满脸堆笑,姿态恭敬:“卫将军,蒋公对您在东北的处境深表同情,知您有难言之隐。只要您答应即刻返回台湾,‘陆军一级上将’的军衔和‘国防部长’的职位,都为您虚位以待。”

卫立煌坐在破旧的藤椅上,静静地听着特使的许诺。他没有看那些金条和美钞,只是盯着特使的眼睛,一字一顿地说道:“请你回去告诉蒋先生,我卫立煌这辈子,打过胜仗,也打过败仗;受过奖赏,也受过冤屈。但我最不缺的,就是官帽子。”
他拿起桌上那封周恩来的信,轻轻扬了扬:“这里,有人情,有信义。这些东西,是你们给不了我的。”
特使悻悻而去。卫立煌对韩权华说:“权华,该做个了断了。”他下定决心,开始通过秘密渠道,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取得联系,商讨回归大陆的具体事宜。
第四章:延安暖阳,一件中山装的情谊
在香港做出回归抉择的那些个夜晚,卫立煌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回到1938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。那段延安之行的记忆,如同暗室中透进的一缕阳光,温暖了他此后数十年的坎坷岁月。
当时,他担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,在山西领导抗战。出于对共产党及其游击战术的好奇与重视,他决定亲自访问延安。

当他的车队抵达延安时,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。没有高大的城墙,没有林立的官邸,只有连绵的黄土高坡和一排排依山而建的简陋窑洞。中共领袖毛泽东,就在一个窑洞外迎接他。
卫立煌望着眼前这位在国民党宣传中被描绘成“青面獠牙”的“赤匪头子”,心中充满了惊讶。
毛泽东身材高大,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,袖口和膝盖处打着补丁,脚上是一双磨损严重的布鞋。他神采奕奕,笑容真诚,完全不像一个手握重兵的领袖,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学者。
“卫将军,一路辛苦!欢迎你到我们这穷山沟里来做客!”毛泽东伸出有力的大手,紧紧握住了卫立煌的手。
“润之先生,久仰大名。”卫立煌连忙回了个标准的军礼。

两人在窑洞里促膝长谈,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。窑洞里陈设极其简单,一张木桌,几条板凳,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。
毛泽东指着地图,从抗日战争的全局态势,谈到国际风云变幻,再到国共两党的合作前景。其见解之深刻,眼光之长远,令卫立煌越听越心折。
当卫立煌问到八路军游击战的精髓时,毛泽东抽了一口烟,笑着解释道:“卫将军,我们的游击战,说起来也简单,就是十六个字:‘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’。核心就是,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,而在于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,保存自己。这叫‘存人失地,人地皆存;存地失人,人地皆失’。”
卫立煌听得连连点头,心中豁然开朗。他由衷地赞叹道:“润之先生,您这‘论持久战’的思想,真是高瞻远瞩,切中要害啊!”
临别时,延安的天气突然转冷,刮起了刺骨的寒风。毛泽东见卫立煌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夹克,立刻转身回窑洞,拿出自己一件崭新的毛料中山装,不由分说地要给卫立煌披上。

“卫将军,天气冷,披上吧,千万别着凉。”
卫立煌连忙推辞:“这怎么行?这是您的新衣服,您自己……”
“拿着!”毛泽东的态度不容拒绝,他硬是把衣服塞到卫立煌怀里,爽朗地笑道,“我们都是打日本鬼子的,都是一家人,分什么彼此!你在前线多杀一个鬼子,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!”
卫立煌接过那件尚带着体温的中山装,手指触到细密厚实的布料,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。他看着毛泽东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旧军装,再看看怀里这件崭新的中山装,一时间百感交集,说不出话来。
这件中山装,从此成了卫立煌最珍视的物品之一。
回到设在洛阳的第二战区指挥部,卫立煌对延安之行的感触依然久久不能平息。他立刻下令,打开自己的军需仓库,给八路军送去一批急需的物资。
副官拿着清单,面有难色地提醒道:“总座,这……这批物资数量巨大,有100万发子弹,25万枚手榴弹,还有180箱牛肉罐头……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,恐怕会怪罪下来。”

“怪罪就让他怪罪!”卫立煌一拍桌子,态度坚决,“八路军是在打鬼子,是在为国家民族流血!我们多给他们一颗子弹,他们就能在战场上多消灭一个敌人!我卫立煌做事,凭的是抗日的良心,不是某个人的脸色!”
正是这次延安之行和这件中山装所代表的情谊,在卫立煌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。这颗种子,在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,终于在香港那个困顿的时期,生根发芽,指引了他最终的人生抉择。
因此,当1949年,身在香港的卫立煌得知母亲在合肥老家无人照料,心中万分焦急时,他第一个想到可以求助的人,便是毛泽东。他颤抖着笔,写下了那封情真意切的信。他相信,那位在延安把新衣赠予他的“润之兄”,绝非无情之人。
事实证明,他没有信错人。当他很快收到母亲安然无恙、并得到当地政府妥善照顾的家书时,这个在枪林弹雨中都未曾掉过一滴泪的铁血将军,一个人躲在房间里,哭了整整一夜。
第五章:归航与新生,历史的最终选择
1955年3月15日,香港维多利亚港晨雾弥漫。一艘名为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的豪华客轮鸣响了悠长的汽笛,缓缓驶离码头。
卫立煌和韩权华站在甲板上,凭栏远眺。渐渐远去的香港岛,在薄雾中轮廓模糊,仿佛他们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,也随之淡去。

“权华,我们回家了。”卫立煌握着妻子的手,声音中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感慨。
经过周密安排,他们的归国之旅进行得十分顺利。客轮抵达广州时,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,亲自到码头迎接。
当卫立煌走下舷梯,看到码头上那个熟悉而亲切的身影时,他的脚步不禁加快了。周恩来也快步上前,在众人瞩目之下,紧紧握住了卫立煌的手,热情洋溢地说:“欢迎你回家,俊如兄!我们等了你很久了!”
一声“俊如兄”,一声“欢迎回家”,让卫立煌瞬间热泪盈眶。他想起十七年前在太原的彻夜长谈,想起在香港收到的那封信,千言万语涌上心头,最终只化作一句哽咽的话语:“周先生……我……我终于回来了。”
不久之后,在北京中南海,毛泽东接见了卫立煌。一见面,毛泽东就笑着迎上来,还是像在延安时那样紧紧握着他的手:“俊如啊,你可回来了!我们都盼着你呢!”
毛泽东特意让人准备了几道卫立煌爱吃的家乡徽菜,为他接风洗尘。席间,两人谈笑风生,仿佛多年未见的老友。
“当年你在忻口那一仗,打得不错,给小日本狠狠上了一课。”毛泽东递给他一支烟,回忆起抗战往事。

卫立煌接过烟,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,烟雾缭绕中,他想起了延安的窑洞,想起了那件中山装,感慨万千地说:“润之先生,我这一生,戎马半世,到头来最后悔的,就是没能早点认清蒋先生的真面目,走了不少弯路。”
毛泽东摆了摆手,豁达地说:“过去的事情,就不要再提了。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嘛。你能回来,就说明你心里还是向着人民的。现在国家百废待兴,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。国防委员会还缺一位副主席,我看,这个位置你来坐最合适,你看如何?”
卫立煌猛地站起身,整理了一下衣衫,向毛泽东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声音洪亮地回答:“立煌但凭党和国家的安排,万死不辞!”
归国后,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等要职,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地位。他积极参政议政,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,贡献了自己的余热。
晚年的卫立煌,深居简出。人们常常看到他穿着那件珍藏多年、已经略显陈旧的中山装,在院子里散步。那件衣服,承载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和最温暖的记忆。
1960年1月,卫立煌因病重住进医院。毛泽东得知后,十分挂念。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,物资匮乏。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,派人买了两条鲜鱼,亲自送到医院探望。

“俊如,身体好些了吗?”毛泽东坐在病床前,关切地握着他消瘦的手。
卫立煌已经十分虚弱,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,用手指了指床头叠放整齐的那件中山装,断断续续地说:“润之先生……这件衣服……我一直……一直留着。”
毛泽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,眼眶不禁湿润了。他拍了拍卫立煌的手背,轻声说:“我知道,我都知道。”
1960年1月17日,卫立煌病逝于北京,享年63岁。弥留之际,他依然紧紧抱着那件中山装,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那个寒冷的延安夜晚,感受着来自一位伟人手心的温暖。
遵照他的遗愿,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墓碑上,镌刻着“卫立煌之墓”五个大字,在风雨中默默诉说着这位爱国将领传奇而复杂的一生。

而那件见证了一段跨越党派的真挚情谊、改变了一位将军命运的中山装,如今作为国家一级文物,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。
它无声地向后人讲述着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,关于选择、信仰和人性的不朽篇章。

